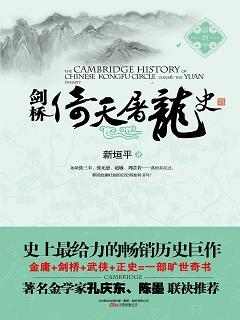- [ 免费 ] 题记
- [ 免费 ] 第一章 绪论
- [ 免费 ] 第二章 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 ...
- [ 免费 ] 第三章 元代门派政治的形成(1 ...
- [ 免费 ] 第四章 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 ...
- [ 免费 ] 第五章 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 ...
- [ 免费 ] 第六章 明教的三十年宗座空位 ...
- [ 免费 ] 第七章 元朝中期政局变动与汝 ...
- [ 免费 ] 第八章 明教的宗教改革与分裂 ...
- [ 免费 ] 第九章 武当的崛起及其与少林 ...
- [ 免费 ] 第十章 光明顶会战和张无忌的 ...
- [ 免费 ] 第十一章 张无忌的统治与新秩 ...
- [ 免费 ] 第十二章 张无忌统治的终结和 ...
- [ 免费 ] 第十三章 从明教到大明帝国(1 ...
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AA+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
繁
第四章 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
2018-9-25 18:38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
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
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
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
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
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
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
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
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
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
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
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
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
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
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
《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
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
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
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
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
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
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
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
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
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
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
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
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
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
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
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
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
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
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
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
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
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
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
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
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 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
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
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
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
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
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
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
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
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
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
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
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
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
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
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
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
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
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
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
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
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
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
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
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
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
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
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
《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
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
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
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
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
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
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
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
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
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
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
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
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
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
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
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
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
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
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
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
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
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
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
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
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 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
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
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
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
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
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
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
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
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
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
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
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
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
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